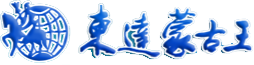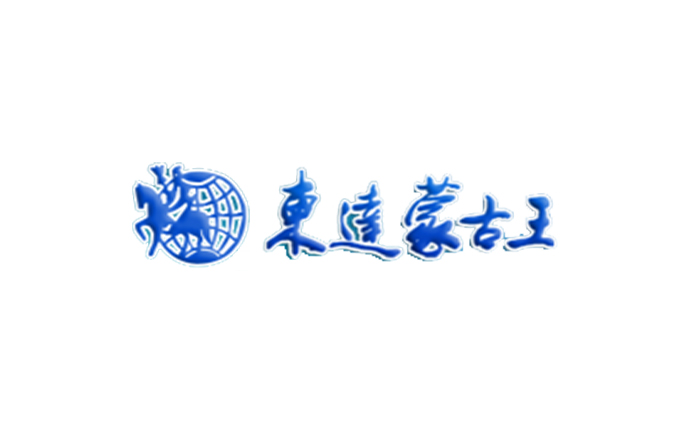集團(tuán)動態(tài)
精耕庫布其(節(jié)選)
一
多少年來,庫布其這句蒙古語,常被人翻譯為弓弦,意即黃河為弓,沙漠為弦。
居住在庫布其沙漠腹地的莫日根道爾計(jì)跟我講,幼年時他最愛做的事就是一次次爬上高高的沙丘,向外眺望著。幼時,小莫日根聽老人們講過許多黃河的傳說,但從未見到過如弓的黃河。阿媽對他說,待他長大一點(diǎn),就帶他到黃河邊上磕頭去。在蒙古語中黃河被稱為哈屯高勒,意即母親河。庫布其人守望黃河,就像守望母親。
眼前不遠(yuǎn)的地方倒是有一汪清水,還有直伸到沙丘腳下的寸草灘。正是有了這汪碧水,這片草灘,這兒才被稱為賽烏素才登,直譯成漢語為有好水草的地方。但家鄉(xiāng)那片好水,茵茵碧草只是留在莫日根道爾計(jì)幼時的記憶里,就像一個遙遠(yuǎn)的夢。
那是一場黑沙暴過后,小莫日根發(fā)現(xiàn)沙丘壓上了他家房屋的后山墻,一群山羊跑上家里的房頂,凄凄地咩咩叫著。房頂縫隙處,窸窸地往下落著細(xì)沙。阿媽瘋一般雙手揮著紅柳編的簸箕,刮著壓在房頂上的沙子,屋子房梁發(fā)出“吱嘰嘰”的叫聲,就像藏著一窩餓極的老鼠。阿爸一身風(fēng)塵地趕回來,毅然決定扒掉門窗木料,選擇一個高處,重砌草坯蓋房。這時,小莫日根才發(fā)現(xiàn)平常羊兒們飲水的那汪清清的淖爾沒有了,沙漠無情地吞噬了那片好水。
阿爸默默地不說話,在一處青草茂密的地方,默默地挖了一眼井,并用干枯的沙柳條子圍了起來。羊兒又有水喝了,小莫日根覺得阿爸就是庫布其沙漠上的羅漢金剛。莫日根道爾計(jì)記不得是哪年跟著父母在庫布其沙漠上扒沙掏沙的。他沖我憨憨地笑著、思索著,是五歲還是七歲?“咳,六十多年了。”他感嘆道。
二
那年,當(dāng)小莫日根舞著雙手開始像阿爸阿媽一樣扒沙挖沙時,有一個叫徐治民的漢族大叔帶著一支治沙隊(duì)伍,開進(jìn)了庫布其沙漠東端一個叫園子塔拉的地方。但他們不是挖沙扒沙,是要把樹、草栽種在荒無人煙的園子塔拉大荒漠里。園子塔拉原本是一片好草場,人們在這里開草原種莊稼,最后起沙了,遠(yuǎn)處的大沙漠,幾場大風(fēng)過后,突兀地出現(xiàn)在開荒的人們面前。他們扒掉門窗,用牛車載著鍋碗瓢盆、鐵鍬犁杖,哼著“二姑舅捎來一句話,口外那兒有好收成……”繼續(xù)走他們的西口了。這是典型的“游種”,開一片草場種幾年地,一起沙子便拔腿就走,再尋新的草地開荒種地,鄂爾多斯人稱之為“倒山種”。
“六月的沙蓬無根草,哪搭搭掛住哪搭搭好……”“倒山種”人們的歌聲刺疼了徐治民。徐治民已經(jīng)不是在口外攬工種地的受苦漢了,而是翻身農(nóng)民組織起來的互助組的組長。老徐帶領(lǐng)的這十幾位翻身農(nóng)民是庫布其沙漠上第一代種樹人。剛開始種樹時,風(fēng)沙大得能把人埋了,栽下的樹苗全被沙壓死。人們這才知道在沙漠上種樹是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人們撥弄著埋在沙里的干枯樹苗,不禁有些泄氣。有人譏老徐:“你這是糟蹋五谷哩!”這是句很重的話,意即只吃飯不干正事。老徐不服氣,他領(lǐng)著人們在大沙子的腳底下栽種沙蒿沙柳,苦干幾年,他們栽活大片的沙蒿沙柳,終于擋住了沙頭。
他領(lǐng)著人們冬天搞擋沙壩,春天栽沙柳,植樹苗,旗里林業(yè)站的人還來專門科學(xué)指導(dǎo),建設(shè)固沙植物網(wǎng)格,規(guī)劃林田建設(shè)。為了保證林木的成活率,老徐還在園子塔拉打了多眼水井。春旱時,老徐就挑水澆樹,老徐和鄉(xiāng)親們的肩膀頭壓出的老繭一層又一層。上世紀(jì)五十年代,老徐領(lǐng)著人們在園子塔拉共營造了十八條林帶,最長的有十五里。一眼望去綠油油的,浩瀚大漠中透出了綠的春意。許多“倒山種”的老戶,又回到了園子塔拉,跟著老徐植樹種草。終于,沙子欺負(fù)不動人,園子塔拉已是滿目翠綠,老徐這才想起,要將自己的家搬進(jìn)園子塔拉,屈指一算,這個棄家治沙的人,已經(jīng)離開家整整七個年頭。
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六十多歲的徐治民仍繼續(xù)帶著鄉(xiāng)親們治沙種樹,一排排小樹苗“嗖嗖”往高躥,老徐的腰卻慢慢佝僂了。有一天,老徐一頭跌倒在治沙工地上,大口大口往外噴血。
鄉(xiāng)親們心疼地說:“老徐這是撅著了。”
“撅著了”的老徐開始護(hù)樹,守護(hù)這片林子,驅(qū)趕著竄入林地啃樹的牲口。誰要是想動他一棵樹,他跟人拼老命的心思都有。上個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達(dá)拉特旗人民政府為年屆八旬的徐治民立了一塊碑,碑文記錄了徐治民老人四十年綠化沙漠的事跡。
1991年的春天,我專門去采訪徐治民老人。那天,他不在家,我默默地看著老人簡陋的土坯房,覺得辛苦種了一輩子樹的老人應(yīng)該過得更寬裕些。他老伴帶我去見老人,路上他老伴告訴我,老徐這些日子心里麻、纏得慌,說是人們想分成材林換錢,老徐就是不同意。有人嫌他擋了財(cái)路,就在碑上亂寫亂畫。老徐很生氣,有空就來碑前看看。果然我在碑前見到了徐治民老人,一個壯漢站在他身旁說著什么。老人穿著一件藍(lán)色的上衣,戴著頂深藍(lán)色的帽子,佝僂著身子,臉板得就像一塊石頭。春天的陽光透過樹的枝條斑駁弄影在他那蒼老的臉上,壯漢幾乎是沖他吼:“叔,你倒是說句話呀!”
他老伴悄聲告訴我,這是老徐的侄子,侄子要建新房,想伐兩株樹,做門窗。已經(jīng)磨老徐幾天了,老伴也勸老徐道:“你倒是給孩子句話呀!”
老人就是不開口,侄子啞著嗓子說:“老叔,咱治幾十年沙圖了個甚?”
這的確是個問題。鄂爾多斯當(dāng)時有這樣的俚語:遠(yuǎn)看是討吃要飯的,近看是治沙站的。還有這樣的話:治沙不治窮,到頭一場空。那年,我采訪庫布其、毛烏素沙漠的治沙者們時,確實(shí)發(fā)現(xiàn)植樹種草與富裕之間還有一段距離。那時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在全區(qū)范圍內(nèi)大興“念草木經(jīng),興畜牧業(yè)”理念。伊克昭盟在鄂爾多斯實(shí)施“兩翼一體”的發(fā)展戰(zhàn)略,即治理荒漠化,美化綠化貧困山地、沙地,甚至為每戶農(nóng)牧民制定了林地、經(jīng)濟(jì)林、水澆地、牲畜的具體數(shù)目。各級政府和鄂爾多斯人民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那時,大漠上,山地間,到處都是重新治理鄂爾多斯河山的壯士。這種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治理模式,呼喚著農(nóng)牧民脫貧致富的雄心壯志,激勵著更大范圍的農(nóng)牧民投身于生態(tài)恢復(fù)和建設(shè)美好家園中來。
那個沙塵暴不斷的春天,我驅(qū)車行駛在鄂爾多斯大地上,深入到庫布其、毛烏素沙漠治沙者的工地,準(zhǔn)格爾山地小流域治理工地,感受這山河巨變,曾為茫茫沙漠上鋪出的星點(diǎn)綠色,多次淚水盈眶。但貧窮的治沙者和治沙者的貧窮始終縈繞在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
三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莫日根道爾計(jì)也已經(jīng)是六十多歲的老人。
這個像他的父輩一樣扒沙掏沙、守護(hù)家園已經(jīng)幾十年的他,也變成了沙漠上的鐵打金剛。幾十年來,莫日根道爾計(jì)和他的家人被沙漠?dāng)f得搬了多少次家他已記不清了,但他仍苦苦死守著賽烏素才登。他守望著這片浸染著先輩骨血的大沙漠,不屈不撓地在這片沙漠里扒沙挖沙固沙,像一匹吃苦耐勞的馬一樣守護(hù)耕耘著先人放牧的草地。他硬是憑著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投入在庫布其沙漠的腹地種出了七千多畝人工森林。其中紅柳、沙柳、楊柴、檸條、沙棘等耐旱耐寒植物,還有無邊無際的牧草,已經(jīng)構(gòu)起了自己的生態(tài)屏障。綠草地上,汪汪的濕地上積起了一片片碧水,茵茵青草向遠(yuǎn)方擴(kuò)展,而逞威幾百年的沙漠已不見蹤影。莫日根道爾計(jì)帶我站在一個高處,極目望著眼前這無盡綠色,感慨地對我說:“就跟做夢似的!”我默默地望著眼前這大海一般的翠綠,心想,沙漠去哪兒了呢?真像莫日根道爾計(jì)說的,這是在夢幻之中?
大型企業(yè)進(jìn)入到治沙領(lǐng)域,給庫布其沙漠的治理帶來質(zhì)的變化。產(chǎn)業(yè)化治沙靠的是政府引導(dǎo),企業(yè)發(fā)揮資金、信息數(shù)據(jù)、科學(xué)管理、新技術(shù)應(yīng)用方面的眾多優(yōu)勢,努力把沙產(chǎn)業(yè)鏈拉長,以惠及沙漠地區(qū)的千家萬戶。庫布其兒女創(chuàng)建的“庫布其模式”橫空出世,引起社會的高度關(guān)注。
現(xiàn)在庫布其沙漠的治理實(shí)踐告訴人們,科學(xué)地利用沙漠、呵護(hù)沙漠、精耕沙漠,是治理荒漠化的有效方式。在鄂爾多斯,無論是領(lǐng)導(dǎo)、專家,還是學(xué)者、企業(yè)家、沙漠治理者,都認(rèn)為沙漠可以“變害為寶”。當(dāng)荒漠化治理進(jìn)入產(chǎn)業(yè)化時代,首先要科學(xué)地認(rèn)識沙漠,去粗取精,提高治理區(qū)的林分和草分,萬不可沉湎于眼前的綠色。當(dāng)沙漠不再流動,不再侵害我們的生存空間時,我們盡量不去打擾沙漠的安靜,而要靜下心來,等待沙漠的自我修復(fù)。而研究沙漠的光能利用,了解沙漠的土壤構(gòu)造以及降水周期變化,地下水位和地上風(fēng)速的變化,了解沙漠動物昆蟲菌類以及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活潑生命,才能使我們的產(chǎn)業(yè)化更加多元化和科學(xué)化。
四
庫布其沙漠上的風(fēng)干圪梁,原本是一片荒漠,幾乎沒有一點(diǎn)生命的跡象,光聽這名字就讓人發(fā)怵。趙永亮及其所創(chuàng)建的東達(dá)蒙古王企業(yè),在這里投巨資進(jìn)行荒漠化改造,使之巨變。而這一切都源于趙永亮在庫布其沙漠上對于一株沙柳和一只獺兔的深度研究和開發(fā)利用。
沙柳是固沙的先鋒植物,易在沙漠里成活,人類不加干預(yù),它只有三年的生命期。沙柳生根較淺,只吸附地表水和土壤營養(yǎng),發(fā)芽抽枝,可供草原食草動物啃噬和人類作為薪柴使用。它的根部積起薄土供沙生草類菌類生長,而三年后自身枯死。這是一種讓人尊敬的植物,它不拼命扎根吸取深層地下水分,根須也不四處擴(kuò)張奪取營養(yǎng)。而沙柳又有平茬復(fù)壯的習(xí)性,通過人類對沙柳平茬,它又可抽枝發(fā)芽,周而復(fù)始,生生不息。但由于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不大,人們往往任其生死,沙漠上經(jīng)常見到枯死的沙柳枝滾成團(tuán),人們背回?zé)鹱鲲?。沙柳纖維長,韌性好,是建造高質(zhì)量密度板的上佳材料。趙永亮于是花重金從德國購進(jìn)先進(jìn)、環(huán)保的熱壓高密度生產(chǎn)線。僅這一條生產(chǎn)線,就能夠消化方圓三百平方公里內(nèi)荒漠生產(chǎn)的沙柳。有了顯著的經(jīng)濟(jì)效益,農(nóng)牧民種沙柳的積極性空前提高,一條先進(jìn)的生產(chǎn)線,帶富了上萬名沙柳種植戶,保證了三百平方公里荒漠綠色常在。
我曾考察過“翻身村”和“烏蘭壕村”兩個沙柳種植基地,那里戶均沙柳業(yè)的收入都在三萬元以上,多的高達(dá)十萬元以上。農(nóng)牧民普遍使用了小巧的電動平茬機(jī),六十多歲的沙柳種植戶李文玉老人告訴我,連他都能掌握使用平茬機(jī)的方法,人們再也不用往手心里吐唾沫、掄老镢頭平茬了。為了降低農(nóng)牧民的運(yùn)輸成本,企業(yè)還在重點(diǎn)的沙柳基地建立了削片廠,就地將原料轉(zhuǎn)化成半成品送往生產(chǎn)線。這樣,大大降低了運(yùn)輸成本,提高了農(nóng)牧民的收入,激勵了農(nóng)牧民種植沙柳的積極性。在綠色中獲取財(cái)富,這是產(chǎn)業(yè)化引領(lǐng)荒漠化治理的獨(dú)有魅力。
一株小小的沙柳,竟被趙永亮舞得風(fēng)生水起……
在風(fēng)干圪梁建立世界獺兔之都,是趙永亮心中的一個夢想。獺兔是從國外引進(jìn)的,其皮毛絨厚密實(shí),肉質(zhì)細(xì)嫩,在國內(nèi)外市場上銷路很好。趙永亮經(jīng)過多次考察、專家論證,決定在庫布其沙漠投資打造世界級獺兔之都,選定的就是風(fēng)干圪梁。這里光照充裕,冬季寒冷,夏季清爽,非常適合獺兔生長。除了皮毛、肉食,其他的產(chǎn)業(yè)鏈也很長。兔的內(nèi)臟,可以喂貂。貂除皮毛價(jià)值外,其內(nèi)臟可以喂狼,產(chǎn)生的糞便是天然的有機(jī)肥料,可以改良沙漠土壤,提高土地肥力。這樣,便可帶動種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食品加工業(yè)等綜合產(chǎn)業(yè)發(fā)展。現(xiàn)在在風(fēng)干圪梁圍繞兔子轉(zhuǎn)的已經(jīng)有一萬多人,其中有科學(xué)家、動物學(xué)家、醫(yī)學(xué)專家,更多的還是當(dāng)?shù)氐霓r(nóng)牧民。標(biāo)準(zhǔn)化的兔舍,建得又高又大又寬敞,每幢兔舍旁都有同樣寬敞明亮的家庭式養(yǎng)兔人住所。我問養(yǎng)兔人李鵬程,在這收入怎么樣?他告訴我,過去他種了三十多畝地,刨去各類費(fèi)用,每年也就收入個兩三萬塊錢。十年前,來了風(fēng)干圪梁,那時艱苦,鏟平了大明沙蓋兔舍,種草種樹。后來包了一棚兔子,收入就上來了。八年來,年純收入都在十萬元以上。
現(xiàn)在的風(fēng)干圪梁已經(jīng)是一望無際的綠色,方圓五十八平方公里被綠色覆蓋,基本見不到明沙。而其帶動的綠色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輻射方圓三百公里。趙永亮認(rèn)為綠色并不是句號,治理荒漠的產(chǎn)業(yè)化應(yīng)是對綠色的深思熟慮、精耕細(xì)作,在綠色中持續(xù)不斷地創(chuàng)造財(cái)富,從而惠及這個產(chǎn)業(yè)鏈上的農(nóng)牧民。
現(xiàn)在風(fēng)干圪梁被趙永亮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風(fēng)水梁。風(fēng)水梁已是市政配套和教育醫(yī)療科研設(shè)施機(jī)構(gòu)齊全、產(chǎn)業(yè)集中的現(xiàn)代化的小鎮(zhèn)。現(xiàn)在鎮(zhèn)上常住居民有兩萬余人,很多在趙永亮的公司里工作,隨著沙產(chǎn)業(yè)的做大做強(qiáng),其遠(yuǎn)景規(guī)劃將建成容納十二萬人的沙產(chǎn)業(yè)城市。
神奇的風(fēng)水梁,富裕的養(yǎng)兔人!庫布其沙漠神話般的巨變,讓人流連忘返。放眼望去,綠色涌來,而沙漠漸漸褪去。即使是大明沙,也在重重綠色的重壓之下,改變了狀態(tài)。在我目及之處,沙漠已由涌動的新月形鏈狀,變成了靜態(tài)的圓形穹頂狀。庫布其沙漠圓潤了,已經(jīng)失去了興風(fēng)作浪的氣勢。根據(jù)水文氣象統(tǒng)計(jì),近十年,庫布其沙漠的降水量在年二百零一至四百四十三毫米之間徘徊,大風(fēng)揚(yáng)沙天氣在年均六次左右。比起治理前的“一年一場風(fēng),從春刮到冬”,降水在一百毫米以下的惡劣干旱天氣,庫布其沙漠的沙生植物已經(jīng)具備了自然修復(fù)的氣象水文條件。對治理區(qū)繼續(xù)實(shí)行精耕,繼續(xù)拉長產(chǎn)業(yè)鏈,使綠富同興蓬勃涌動、同生共長。
當(dāng)我見到一粒沙子在顯微鏡下的狀態(tài)時,不禁驚呆了:那是紅色、黃色、綠色、藍(lán)色、紫色等各種色彩的晶粒組合,就像一顆顆晶瑩燦爛的寶石熠熠生輝。我猛然覺得,這仿佛預(yù)示著庫布其沙漠的燦爛未來。是庫布其的沙漠兒女給了庫布其精氣神,給了千古荒漠這般好容顏。庫布其兒女精心守望著這美麗的家園,一往無前地辛勤建設(shè)著這幸福的家園。沙漠兒女敞開大海般的胸襟,擁抱著新時代的八面來風(fēng),科學(xué)地與沙漠共舞共歌。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心中的一個夢,為了金山銀山般的綠水青山永駐人間!
哦,庫布其喲庫布其……
(人民日報(bào) 肖亦農(nóng))